所有原本在屏息圍觀的人全部呆住了。
克雷蒂安和特洛瓦對視一眼,躲在另一輛車裏偷看的卡米拉和安也彼此對視一眼。
已經捂着鼻子往船那邊走的絡腮鬍回過頭來,僵在原地一動不動。
等等,剛剛發生了什麼?
怎麼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了?
再神秘強大的氣質,當脖子卡在結他里後,恐怕也難以讓人覺得神秘,而事實上這人的神情比剛剛被砸了鼻子的絡腮鬍還呆滯。
圍着馬塞內古的靈性之牆已經坍塌,他頗為艱難地噎了口口水。
那個傻逼「指路人」不躲,他大概懂,可為什麼這個高位階『花觸之人』也不躲?為什麼不反擊而同樣是一副被結他扣懵了的樣子?
「游吟詩人的魅力真大啊,我後悔小時候沒有好好練琴,不然我現在至少......」馬塞內古感到大受震撼,開始喃喃自語。
眾人只圍觀到表象,花衣男子自己才知道是什麼感覺。
他已經是初入九階的高位階,剛剛卻只覺得靈性被某種層次遠高於自己的、帶有閃電特性的無形閉環給圍住了,隨着范寧取下紫色琴弦後,束縛感少了一些,但只要自己調用的念頭稍有一個豁口,立馬就傳來一陣麻痹和刺痛的殘留感覺。
而琴匣中那些尖銳的木刺,全部受到了莫名的無形之力控制,凌空懸浮在自己的頸部,並已刺入皮膚之中,離動脈血管只有薄薄的一層,隨時可能更進一步!
「??賠錢?」范寧再度開口後,眾人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花衣男子的手開始哆哆嗦嗦在口袋摸索,又顫顫巍巍遞過去。
「你這隻有1鎊啊。」范寧說道。
「不,不好意思」男子再度摸索,然後遞出了一枚大一號的、5鎊面額的金幣。
那些木刺碎片在下一刻結束了蓄勢待發的狀態,過於迫在眉睫的威脅感消散,但它們仍然扎入皮膚之中,仍然離動脈血管只有一線之隔。
男子小心翼翼地試着動了動結他,立馬傳來一陣尖銳的刺痛,而靈性中仍然帶着電流的麻痹感,他蹩手蹩腳調整了半天,也沒能做出實質性的進展來。
「你錢已經賠了,要不,回去了再慢慢取?」范寧用商量的語氣問道。
「啊??可以,可以」
這人覺得靈性的麻痹感稍有緩解,但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,他頂着把結他轉身,搬運金幣箱子的人也開始撤退。
「失色者」雖然也是稀有人群,但搜索尋覓起來目標並非唯一,相比之下「七重庇佑」更為珍貴重要,之前在這一點上沒出茬子就行,他現在只想趕緊離這個實力難測又行事無常的游吟詩人越遠越好。
星光照射的沙灘上,最後走在後面的兩人,一人捂着鼻子,還有一人形自走結他,場面十分荒誕又滑稽。
「叮——」
那枚殘留着攜帶者靈性的金幣,被范寧指甲掀飛又捏住,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這行人的背影。
隨後眼神又落在了那金燦燦的兩個鐵箱上,商隊派的人正在抬它們,另外的人則重新圍着鐵板、鍋爐和爐台落坐,準備炮製享用豐盛的晚餐。
范寧不清楚「七重庇佑」的具體作用,但教會在「花禮節」的祭典上需要一些非凡物品,這是很正常的事情,從與民間商隊的合作方式上看符合邏輯,也講誠信地歸還了押金、兌現了報酬。
可為什麼剛剛那個人還需要「失色者」的血液?這難道也和「花禮節」有關?似乎不太符合「芳卉詩人從不觸碰失色者」的常識邏輯。
「無助之血」有什麼特殊的用途嗎?
范寧凝望思考之時,遠處的汽渡船已開動,這場變故最後鬧劇式地收場,所有人都暫時鬆了口氣,也越發覺得這個隨行的舍勒深不可測。
克雷蒂安和特洛瓦在感激道謝。
「舍勒先生,對不起教會以後會不會找您的麻煩?」露娜卻是惴惴不安地道歉。
「教會?」范寧將目光從汽渡船上收回,「就算是教會,至少來個主教再來和我說話。」
自己又沒殺人或干涉商隊交付他們「七重庇佑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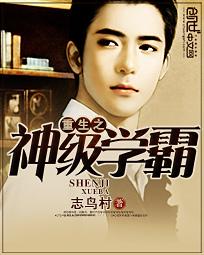 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
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 醫鼎 天才少年,得上古傳承,醫必死之病,滅至強之人。
武聖之拳,華佗之針,北踢蒙教,南降巫蠱,東滅倭寇,西抗十字教,坐鎮神州。
這是一個少年的逆天之路。
醫鼎 天才少年,得上古傳承,醫必死之病,滅至強之人。
武聖之拳,華佗之針,北踢蒙教,南降巫蠱,東滅倭寇,西抗十字教,坐鎮神州。
這是一個少年的逆天之路。
 重生完美時代 老牌程序員出身的李牧,被命運一腳踹回了2001年高考的當口,他欣喜的拍拍屁股,起身便踏上了一條註定牛X的道路。 重活一回,李牧有他自己的追求,賺錢只是牛X的初級階段,至於登上時代周刊、制霸I
重生完美時代 老牌程序員出身的李牧,被命運一腳踹回了2001年高考的當口,他欣喜的拍拍屁股,起身便踏上了一條註定牛X的道路。 重活一回,李牧有他自己的追求,賺錢只是牛X的初級階段,至於登上時代周刊、制霸I